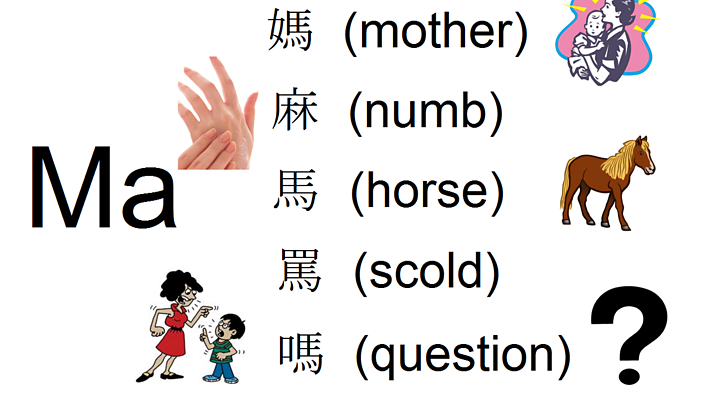多謝晨星辰
琼瑶的最新文章:
【再寫《握三下,我愛妳》】
2010年10月14日,我接到好友王玫的電話,她第一句話就說:
「瓊瑤姐,我們今天早上,為劉姐做了氣切的手術!」我的心砰的一跳,驚呼著喊:「氣切!」
劉姐,在影劇圈中,大家都這樣稱呼她,就像稱呼我「瓊瑤姐」一樣。但是她直呼我瓊瑤,因為她堅稱我比她小。她是我的老友,工作夥伴,我的導演,在我的人生和她的人生中,我們彼此都佔據著相當大的位置,她的名字是「劉立立」。
第一次見到劉姐,是1976年,我拍電影《我是一片雲》,她是那部電影的副導。我從沒見過嗓門這麼大,活力這麼旺盛,工作能力如此強的「女人」,她給我的印象太深了。到1978年,我跟她說:「妳來幫我當導演,妳行!」她對自己完全沒把握,我堅持說她行!於是,她導了我的《一顆紅豆》,從此開始了她的導演生涯。所以,她常對我說:「妳是我的貴人,妳改變了我的命運!」
我和劉姐就這樣成為工作夥伴,我用「喬野」為筆名,編了許多電影劇本,都是她執導的。我們交換著彼此的感情生活,交換著彼此的心靈秘密,也分享著共同為一部戲催生的喜悅。在電影的極盛時期,我們每次票房破紀錄,就要在我家開香檳,那時工作人員、演員和她的另一半----董哥全到齊,笑聲鬧聲驚天動地。當我把電影公司結束,她進了電視圈,把我也拉下水,我們又拍了《幾度夕陽紅》、《煙雨濛濛》、《庭院深深》、《在水一方》……等一連串的電視劇。我和她,就這樣成為一生的知己。
劉姐的感情生活是不可思議的,她年輕時,是風頭人物,是「校花」。董哥是她的學長,都是政工幹校(今國防大學政戰學院)戲劇系的學生。劉姐風頭太健,很多學長追求,大家比賽寫情書給她,打賭誰能追到手。董哥也是其中之一。但是,直到董哥畢業,這些學長誰也沒追到她。
沒多久,董哥結婚了,娶了王玫。當劉姐畢業,進了影劇圈,董哥也進了影劇圈,他們都從「場記」幹起,兩人經過許多曲折,居然電光石火,陷進一場驚天動地的戀愛。但是,此時的董哥已「使君有婦」,兩人只能在外面租了一間房子同居。董哥有才華有能力,是各方爭取的「名副導」,跟劉姐這場戀愛,風風火火,充滿了戲劇性。劉姐性情激烈,曾經為了和董哥爭吵,一刀砍在自己的胳膊上,頓時血流如注,差點沒把手給砍斷。(那是一本巨大的書,無法細述)
當時,王玫已經生了一個女兒,卻仍然在藝工總隊表演。當王玫知道董哥有了外遇,她沒有吵鬧,默默忍受著心裡的不滿。有一次,董哥到南部去工作,王玫也到外地去表演,才一歲多的女兒雅莊,交給祖父母照顧。不料女兒半夜發高燒,持續不退。祖父母找不到王玫和董哥,卻找到了劉姐。劉姐一聽董哥的女兒生病了,急得二話不說,直奔祖父母家,抱起雅莊,就飛奔到當時台北最好的「兒童醫院」。那時可沒健保,兒童醫院收費極高,診斷後要住院。劉姐沒錢,把家裡的電鍋、熱水瓶……各種可當的東西全部典當,再抱著自己的棉被去醫院照顧雅莊。當王玫回到台北,驚知女兒病到住院,急忙趕到醫院裡,卻看到一幅畫面:雅莊蓋著劉姐的棉被睡著了,劉姐搬了一張小板凳,坐在病床前,手摟著雅莊,累得趴在床沿上,也睡著了。王玫驚愕的看著,眼淚忍不住滾滾落下。一顆母親的心,和一個妻子的心,在剎那間融成一顆「大愛之心」。
等到董哥從南部回到台北,才大吃一驚的發現,王玫不但和劉姐成了最好的朋友,還把劉姐接到家裡,兩個女人說,願意分享一個丈夫!董哥不敢相信,卻喜出望外的接受了這個事實。
從此他們過著三人行的生活。王玫陸續又生了兩個孩子,都把劉姐當成親媽一樣,稱呼劉姐為「好媽」。劉姐對這三個孩子,更是寵愛異常。尤其是小兒子「四海」,幾乎是劉姐抱大的,劉姐愛這兒子到無以復加,連我旁觀的人,也歎為觀止。劉姐也為了這段愛情,為了尊重王玫,終身不要生孩子,免得孩子們之間會產生問題。
問世間情為何物?我實在不明白。年輕時,沒有人看好他們這種關係,總認為隨時會鬧翻,會弄得不可收拾。但是,他們就這樣恩恩愛愛的生活著,數十年如一日。當年,我也曾私下問劉姐:「妳終身認定董哥了嗎?未來是妳不知道的,會不會再遇到別人?」她斬釘截鐵的回答我:「絕不可能!我認定他了!」
劉姐當導演,收入比當副導演時,當然好很多。董哥也當導演了,卻沒有劉姐勤快,接戲比較接得少。劉姐把賺的導演費,除了少數寄給父母,少數自用,其他都用在董家。董哥才氣縱橫,每次劉姐接到劇本,都是董哥先幫忙看劇本,然後和劉姐討論,再幫劉姐分鏡頭。因此,兩人的工作是密不可分的。王玫就專心持家帶小孩,三人一心,把孩子一個個拉拔長大。他們這一家人,成了很奇妙的一種「生命共同體」。最讓我感動的,是王玫數十年不變的那顆無私、寬宏、包容的心。她不止包容,還深愛著劉姐,有次甚至對我很真心的說:
「我沒什麼學問,也不太懂電影,看到他們兩個一起工作分鏡頭,總覺得他們才應該是一對夫妻,我好像妨礙了他們!」言下之意,還很歉然似的。
一年年過去,當劉姐年紀老了,不再能風吹日曬幫我拍戲了。我和她的友誼不變。每年過年前,一定要見一面,談談彼此的生活。2007年,劉姐和董哥來我家,我發現劉姐講話有些口齒不清,走路也歪歪倒倒。董哥才告訴我,劉姐患了遺傳性的一種罕見病「小腦萎縮症」。我頓時目瞪口呆,我看過一部日本電影,名字叫「一公升的眼淚」,內容就是紀錄一個患了這種病的女孩,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。當我嚇住時,反而劉姐安慰我,她說:「我母親有這種病,它會讓人逐漸失去行動能力,逐漸癱瘓,無法說話。但是,它不會影響智慧和生命,我母親發病後,還活了二十年!」董哥在一邊接口:「二十年夠了,這二十年,我和王玫會照顧她!」
那天,看著董哥扶持著劉姐離開我家,我的眼淚在眼眶裡打轉。我立刻衝到電腦前,去搜尋「小腦萎縮症」的資料,發現確實像劉姐說的,如果是老年人發作這病,不會影響智力,但是,會逐漸失去所有生活能力。我想到,劉姐是這麼有活力的一個人,怎能忍受逐漸癱瘓的事實?如果失智還好,反正自己都不知道了!假若思想一直清晰,卻連表達能力都沒有,那不是禁錮在自己的軀殼裡了嗎?到那時候,董哥和王玫還有耐心和能力來照顧她嗎?畢竟,董哥和王玫也老了,董哥自己身體也不好。
從那時起,我和王玫就經常通電話,談劉姐的病情。劉姐沒有她說的那麼樂觀,她的病惡化得很快,從發病到不能行走,到說話完全不清,在三年中全部來臨。王玫每天要把她抱上輪椅,抱上床,幫她洗澡,餵她吃飯,推她去外面散步……家裡還有新添的小孫子,可以想像生活多麼艱難。我力勸她請外籍看護來分擔辛苦,如果王玫也倒了,誰來撐持這個家?她聽了我,請到一個很好的印尼看護。
然後有一天,王玫告訴我,劉姐因為肺部感染,進了加護病房,現在插管治療,說不定會挨不過去。我難過極了,談到傷心處,不禁哽咽。我當時就要求王玫,如果到了最後時刻,千萬不要給劉姐「氣切」,因為「氣切」會延長生命,卻無法治療這個病,還不如讓她走得乾脆一點。我自己,早就寫好放棄急救的文字,並且交待我的兒子,絕對不可氣切和電擊,時候到了,就讓我平安的走。
因此,當我聽到王玫說,幫劉姐氣切了,我才震懾住。我問為什麼還要氣切?王玫哽咽著說,不捨得啊!插管已經把她的喉嚨都插破了,醫生說,有人八十歲氣切後還救了回來,何況,劉姐還有意識,會用眨眼表示意見,當他們問她要不要氣切時,她皺眉表示不要。但是,王玫問她,妳不想回家嗎?妳不想看兩個孫子嗎?劉姐又連連眨眼了!王玫說:
「她還有生存的意志,她還能愛啊!我們捨不得放棄她呀!」
談到這兒,王玫忽然對我說:「我和董哥離婚了!」
「什麼?」我驚問。「這個節骨眼,你還跟董哥鬧離婚?」
「沒敢跟妳講,」王玫歉然的說:「我們離婚後,十月三日那天,董哥在醫院裡,和劉姐結婚了!總得讓她名正言順當董太太呀!萬一她走了,我兒子才能幫她當孝子,捧她的靈位呀!」
我握著電話筒,久久無法說一語,眼淚在眼眶轉,聲音全部哽在喉嚨口。王玫在電話那頭也沙啞難言,董哥接過了電話,繼續跟我說。告訴我整個離婚結婚的提議,是兒子四海提出的。因為他要當劉姐名正言順的兒子,為劉姐當「孝子」。
結婚以前,他們去病床前,把離婚證書亮給劉姐看,董哥說:
「我可以娶妳了!妳要不要嫁我?」劉姐眼睛濕了,眨了眨眼。表示願意。
所以,十月三日那天,醫生和護士們,把病房佈置成新房,貼了囍字,還有一束氣球。區公所的職員被請來,到場見證(因為要辦理結婚戶籍)。大家圍繞著病床,一起唱著《庭院深深》,和其它的電視主題曲。劉姐笑了,她已經很久沒有笑過,但是,她笑了……董哥就這樣娶了和他相愛了四十幾年,現在躺在病床上不能動的新娘!
我聽著,哭了。我說:
「董哥,你生命裡,有這麼偉大的兩個女人,你也沒有白活了!我該不該說恭喜你呢……」我說不出話來,心裡是滿滿的感動和激動。王玫又接過電話,跟我說:
「雖然沒照妳的意思做,我們幫她氣切了,醫生說,氣切之後可以活很多年。劉姐還有多久,我們還不知道。如果狀況穩定,兩星期就可以出院,我會把她接回家,有孩子孫子包圍著,她一定比較快樂!今天,我去醫院看了她,我握住她的手,妳知道嗎?她居然回握了我幾下!好像在跟我說什麼!」我心裡一震,想到曾經告訴劉姐,《敲三下,我愛你!》的故事,當時還想拍成電影。(那故事收在我《不曾失落的日子裡》,劉姐非常喜歡)。我頓時知道了,劉姐在對王玫說:「握三下,我愛妳!」
這是我身邊的故事,最真實的故事,聽了這故事,我一直激動著,想到大家在醫院裡唱《庭院深深》的婚禮,想著我的好友劉姐和她的一家,我什麼事都做不下去。我的眼睛不曾乾過,好想哭。但是,想到劉姐在生命的尾聲,迎來這樣一個婚禮,她一定得到莫大的安慰!她一生付出這麼深的愛,董哥和王玫,也用這麼深的愛來回報她!她也值得了!如果,我們這個社會,不用批判的眼光,來看待各種愛情,也能欣賞容納這樣的愛,那有多好!何況,現在連同志都要立法結婚了!
人類的愛是很複雜的。我有一個朋友研究科學,他告訴我,宇宙中有龐大的星系,每個星系可能都大於我們的太陽星系,當兩個中子星合併時,會發生巨大的力量,叫做「重力波」。「重力波」會產生一種時空漣漪,轉變時間和空間,影響巨大。他說:「人與人不可思議的相遇和感情,可能就是重力波造成的,沒有對錯,因為重力波強大、註定、而無從逃避。說不定今天的你我,早就在幾億年前某個星球裡相遇過,所以才有『似曾相識』和『一見鍾情』的事發生。」
我不懂科學,在寫這篇文章的今天,「重力波」已經在2017年10月16日被人類直接探測到而證實了。但是,愛因斯坦早在一百年前就預言過,當時無人相信。這和劉姐、王玫、董哥的故事有關嗎?我那相信科學又相信愛情的朋友說:「如果你相信重力波,你就會相信世間所有不可思議的愛情!」
知道劉姐和董哥結婚那天,我的心情無法平復,我要把這個故事即時寫下來,這故事裡不止有愛情,還有你我都無法瞭解的大愛!為什麼還有人不相信「人間有愛」呢?我祈望劉姐能夠早日出院,回到她新婚的家,再享受一段親人的愛!因為她還有知覺,還有意識,還能愛!
今天,是2017年10月30日,距離劉姐氣切,已經七年。我重新整理這篇《握三下,我愛妳!》因為七年間,我發生了很多事情,鑫濤失智,我心力交瘁的照顧,在他又大中風後,我遷就鑫濤的兒女,違背他的意志,幫他插了鼻胃管。當初,我請求董哥夫婦,不要幫劉姐氣切,結果還是氣切了,過程幾乎一樣。這七年裡,董哥和王玫照顧著劉姐,在一次次反復肺炎之後,終於長住於醫院。王玫開始奔波於醫院和家裡,幫劉姐逐漸變形的身子,親自擦拭,一面擦拭,一面告訴劉姐家裡的種種大事小事,不管劉姐能懂還是不能懂。劉姐再也無從表達,成了標準的「臥床老人」。
2015年8月,董哥因肺氣腫病危住院,對王玫說:
「如果我的時間到了,什麼管子都不要幫我插,立立的悲劇不能在我們家發生兩次,我不要像她那樣活著!」
王玫點頭答應,董哥住院後,把氧氣罩拿掉,對王玫說:
「我想唱歌!」
他對王玫唱了兩首歌,一首是《一簾幽夢》,一首是《感恩的心》,握住王玫的手,在王玫對他表示,會繼續照顧劉姐之後,帶著淡淡的微笑,離開了人世。
照顧者比被照顧者先走,是常常有的事。我前兩天才去看鑫濤,我檢查他的手,檢查他的腳,告訴他我來了!他完全沒有反應,我看著那已經變形的手腳和傴僂的身子,知道即使如此,他還是可以在管線和醫藥下「活」很久。我忍不住對他低低說:「可能我無法送你走,看樣子,我會像董哥一樣,比劉姐還先走!」
回家的我很悲哀,想著劉姐的故事,我告訴自己,我要把《握三下,我愛你》再整理重寫一遍。劉姐還活著,七年了!鑫濤也還活著,整整住院608天了。我想起,在我出版《雪花飄落之前》時,辦了一個「新書座談會」,在座談會上,和幾位醫生談論「臥床老人」和「插管問題」。座談會結束後,我走下台和來賓們擁抱,不料王玫也來了,她抱住了我,哭著在我耳邊說:
「瓊瑤姐,看了妳的書,更加明白了!當初沒聽妳的話,我們錯了!不該幫劉姐氣切的!」
我忍著淚,緊緊的擁抱了她一下,偉大的女人,常常隱藏在社會的小角落。還要被這個社會「道德的眼光」批判。我知道,她仍然在幫劉姐擦澡,仍然每隔一天去照顧她丈夫的女人!哦,錯了,她已經離婚了。是去照顧她那已逝的「前夫」的「妻子」!
真實的故事,一直在我身邊演出。
明天,我想去醫院,只為了去握三下鑫濤的手!
瓊瑤
2017.10.30,寫於可園
⌘ 從我的 iPhone 傳送 ⌘